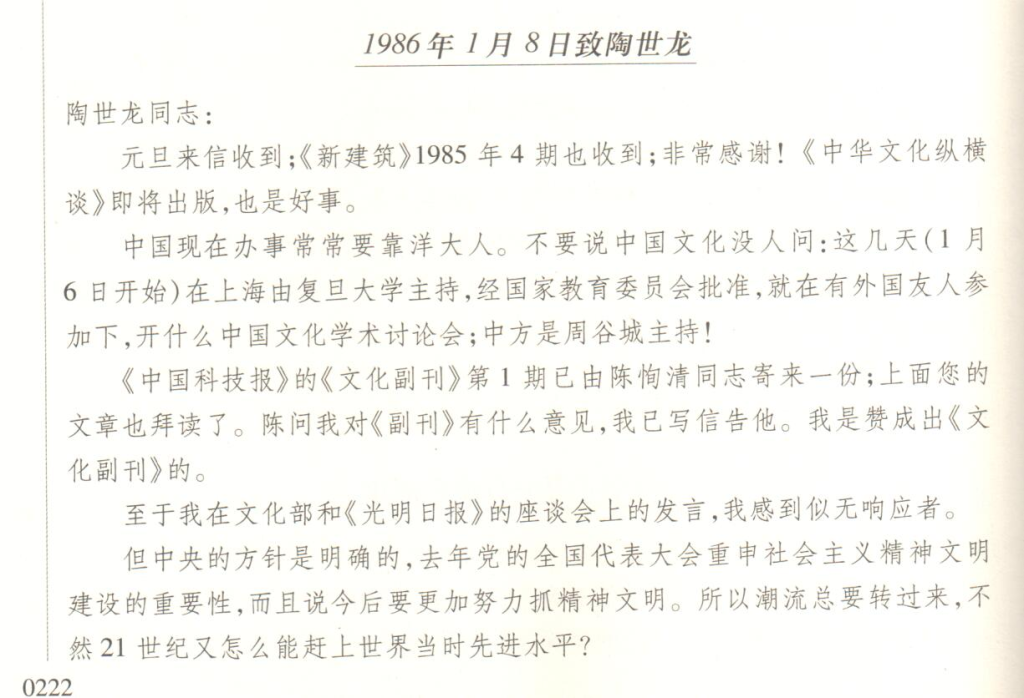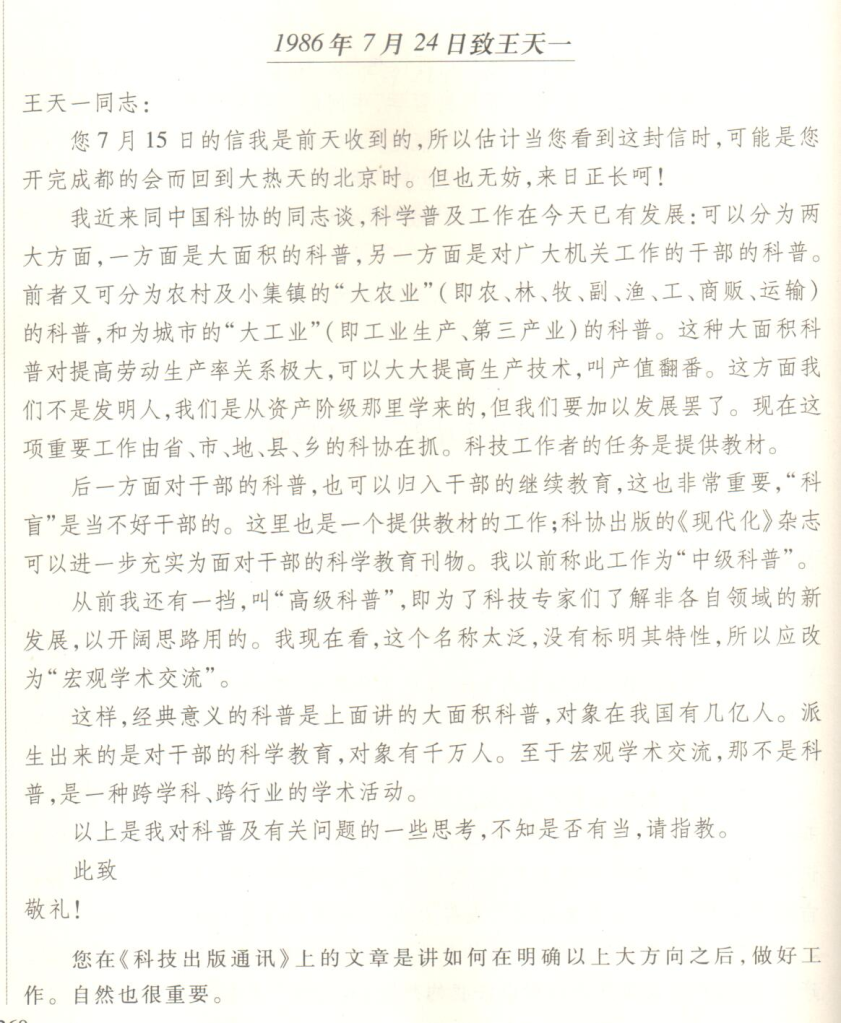据网名【九夜】在信息交流中保存的文本重新发出。
2019-03-30
陶世龙:愚公的误会
Posted June 27, 2013
五柳村编者按:本文曾于2004年发表在《三思科学》复载于人民网和五柳村。写这篇文章,是因愚公之志固可嘉,愚公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可取,缺乏科学思维之故。希望通过纠正这一已广为传播的概念,引起对科学的重视。今见《 中国青年报 》发表的王学进《愚公移山精神研究会能研究什么》一文( 2013年06月27日)指出,如用今人的眼光解读愚公精神,可以得出好几种否定性评价,论述周详,许多见解与当年本文所见相合。人民网上的这篇文章还在,遂据以再在五柳村介绍出来,—2013年6月27日。
人民网>>科技>>科技专题>>大话科学·陶世龙专栏>>科技评论
走出认识地球的误区(五):愚公的误会
陶世龙
2004年11月15日13:46

(喜马拉雅,地球的脊梁。NASA空间照片)
愚公移山的故事,流传很广,智叟认为愚公想以一家之力,把太行、王屋这样的大山搬掉,办不到。愚公说:“虽我之死,有子存焉;子又生孙,孙又生子;子 又有子,子又有孙。子子孙孙,无穷匮也。而山不加增,何苦而不平?”于是智叟无言以对,成了被嘲讽的对象。
愚公一家可以生殖繁衍,而 山不加增,至少在辩论上听来似乎有理,但他这个理论的基础实际上不存在,因为太行山,还有中国许多高山,都是近千百万年来一直在上升,喜马拉雅山更为显 著,近期测得的数据,一年升高5-10毫米。珠穆朗玛现在是世界最高峰,可原来是海底,在不到200万年的时间内,从和海平面一样高,进而达到现在的高 度;须知它在升出海面后便要受到各种自然力的破坏剥蚀,今天的8848米,是抵消了这些损耗的结果。如果它在成为山后便不再上升,早就天然地夷平了。
山的上升,也就是体积在不断加增;上升1毫米,意味着1平方公里面积上要增加1000立方米的土石方,重几千吨,以太行山之大,愚公一家三个劳动力,又是要运到渤海去,一年才能往返一次,他们搬走的远不如加增的多,愚公立论不能成立,但智叟也没有懂得这一点。
当然,这也不能简单地说愚公和智叟都没智慧,那时的人,只能靠自己的感觉器官来观察自然,而像山的上升,即便是一年100毫米,也难以察觉的。所以在古 代,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,人们普遍以为山、连同整个大地都是稳定不变的。稳如泰山成为无庸置疑的观念,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,”的哲学,长期是中国社会中的 主流思想。
不过也不是绝对不能认识,因为可以从自然界一些事物的变化来比较分析,中国古代便有过“高岸为谷,深谷为陵”,“沧桑多 变”这类认为地面形态会变化的思想。遗憾的是,中国的古代贤哲,缺少对自然认真地探究,而且在“天人感应”的思想指导下,即使地面的形态出现了明显的变 动,如大地震发生时地裂山崩,也不就自然本身去寻找原因,而用这是上天的惩罚来解释。愚公移山这样带有神话色彩的寓言,没有人从科学的角度去考究,更不奇 怪了。
地质学的建立,纠正了愚公的误会,人们可以从构成这些大山的地层及其中包含的化石,判断出它发生过的变化。太行山、喜马拉雅山还在上升,都是运用地质学的知识与方法,找到了证据才说的。
峡谷的出现。就是山体还在上升的有力证据,因为只有山体持续上升,河流中的水才会持续向河床底下的岩石冲刷侵蚀,使它不断加深,成为陡峭壁立的峡谷,正 因为如此,所以喜马拉雅山区能有世界第一的大峡谷。太行山中也有峡谷存在。北京的西山是太行山的馀脉,南口、居庸关一带便有曾为文人雅士游览刻石的小型峡 谷。
河流两侧出现的台阶状的平地,证明这里曾经稳定而又升高。
因为河流下蚀的深度,受到它要进入的湖或海的水面 高度的限制,在那里的海拔高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,便会到达下蚀的极限,转为向两侧侵蚀,使河滩的面积扩大,成为平地的开拓者。这些平地当时是和河流水面差 不多高,涨水时就会被淹没,给河滩淤积泥土,布满卵石;现在高出河面很多,离河岸也远了,昔日的河滩,升高为今天的阶地;在阶地上可以找到河边才有的卵 石。有力地说明了地势的升高,
一个地方出现的阶地,常常从上到下有多级,说明这里升起又暂时稳定下来不止一次。
在北京西山,阶地是很容易见到的,明十三陵便都是建造在阶地上,北京猿人居住过的周口店也有。
所以要找寻山在上升的证据并不难。当然,要是没有地质学的知识,看见了也只能失之交臂,而地质学的知识越多,找到的证据也越多。譬如说构成珠穆朗玛峰的 岩石是石灰岩,便可证明珠穆朗玛峰原来是海底,因为石灰岩一般是海里形成的,找到只有海洋里才能生存的生物的化石,证据就更充足了。喜马拉雅山上找到过多 种海洋生物的化石,其中鱼龙的化石特别引人注目,鱼龙不是恐龙,只是海里才有。
在喜马拉雅山上,海拔4000-6000米的高度,发现了今天只能在低于2000米高的地方才能有的植物化石,也可以证明这里原来处于较低的位置,而在测出积累这些岩层需要的时间后,更可算出它上升的速度了。
现代的大地测量,特别是用激光来测量距离的方法出现以后,地面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微小变化,都能即时查出。山体有没有上升,更可以直接观测判断了。
当然,也不是说地球上的山,现在都还在升高,只是一部分,但恰恰在中国是如此。这是地球最近历史时期,在岩石圈中发生的两个相邻板块撞击的最强烈地质事 件,正好发生在我国西南边境一带。原本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印巴次大陆向北移动,终于碰撞在一起,中间的结合部位受到挤压,隆起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,我 国广大地区都受其影响。象太行山在一亿多年前形成后,本已趋向稳定,顶部的峰峦,已因受到风化剥蚀而消失,变得比较平坦;河流的两侧也因流水的侵蚀和堆 积,开拓出小块平地。但随着喜马拉雅山的上升,太行山也再一次升起而有了今天的形态。我国境内的山,大多有这样的经历。远在加拿大东海岸从东北向西南延伸 到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和欧洲与亚洲之间的乌拉尔山,则没有受到多大影响,便都已变得比较低平,自然界倒是真有这样的“愚公”,把破坏了的山石沙土搬到海里 去,主要是流水的作用。
当然,编制愚公移山这个带有神话色彩寓言的作者,并不是在探究自然,而是借题发挥,用来赞扬那种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作用的坚韧不拔的精神,同时也是在显示他辩论的智慧。但他的立论经不起科学的分析,科学要求事实为基础,但愚公则并不考核事实。而且即便如所想象的 “山不加增”,像他的做法也是不现实,不可取的,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好空谈,不务实,缺少科学精神的缺陷。
我发现有位网友雨声就此提出疑问,他说:
关于“愚公移山”,我从哪个方面都想不通。 他想把山搬走,就不说现代的环保和生态的观点,也不说他对邻居等的影响,仅仅从他个人的利益说,他也是得不 偿失的。您想呀,他家面前有座山,影响了他的出入,他感到不方便,他可以搬家呀,那才需要多少时间和金钱呀?!他偏不!他要搬山!那山是好搬的?!他还有 理:我搬不完,有儿子,有孙子,子子孙孙无穷尽也!!!……
呜乎哀哉!几代的人就为了搬山?!搬山为了什么?为了出门方便?!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以及精力都花费在这方面上?—怨不得中国这样呢!
有人说了,愚公移山只是说明了一种精神!
我真不知道这种精神是什么。请问:那山最后是怎么搬走的?—是“神”移走的!
这就是愚公的精神吗?!
雨声时空http://yusheng.boy.net.cn/index.htm
问的好!愚公移山故事的流传和受到欢迎,正好给那种大赞“天人合一”是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协调的说法打了一记耳光。
愚公移山的故事首见于《列子·汤问篇》,《列子》据说是战国时人列御寇(或作 列圄寇)所著,此人据说能御风而行,后来成仙了,后世把他归入道家一类。 当时诸子百家争鸣,为压倒对方,常假托远古不可考的故事乃至神话以逞口舌之辩,其间不乏卓越的思想火花,但同时颇多惑人的诡辩,而不必以事实为依据,仅出 于一己之玄想的也不少。
比起来,孟子说“挟泰山以超北海,是不能也,非不为也。”倒是务实的态度,但似乎人们更喜欢那种空泛的豪言壮语,想成仙的总是比不相信神仙的人要多。
在有个网站上看到一个什么修炼人发表的对愚公移山的看法,更使我吃惊,因为他说:“愚公原来是个神,故事中的智叟原来是个常人。师父说:‘佛、道、神他 们没有人的观念,没有常人这种思维方法’。……如果你是以一个神的想法去对待问题,自然会带来神的状态;如果是以一个常人的思维对待自己遭遇到的问题,当 然见到的也就是人的景象。愚公对待家门前的两座大山,没有常人心,神迹显现了。而那位‘智叟’则会永远迷在常人的假象中兜圈子。
可谓语无伦次,但他是煞有介事。世界已进入科学时代的今天,实在是应该自省了。
当然,对于古人,是不必也不应责难的,那时人类还处于童年时代,对自然、对地球的认识,自然具有童年幼稚的弱点。就是地质学对地球的认识,也是在不断纠正谬误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。譬如对喜马拉雅山的形成,便有过多种解释,就是在今天,也不是什么都清楚了。
地壳是地质学中一个常用的名词。地壳运动也已为大家所熟知,用地壳运动强烈来说明地震的发生、山的形成,大家也多能理解。但当初地壳这个词的提出,其实也是出于误会。
所以出现认识的错误是不足怪的,重要的是能不断发现和纠正错误的认识,这正是科学的特点,在地质学的发展中,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[附录]《列子·汤问篇》中“愚公移山”故事的原文:
太行、王屋二山,方七百里,高万仞。本在冀州之南,河阳之北。北山愚公者,年且九十,面山而居。惩山北之塞,出入之迂也,聚室而谋曰:“吾与汝毕力平 险,指通豫南,达于汉阴,可乎?”杂然相许。其妻献疑曰:“以君之力,曾不能损魁父之丘,如太行王屋何?且焉置土石?”杂曰:“投诸渤海之尾,隐土之 北。”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,扣石垦壤,箕畚运于渤海之尾。邻人京城氏之孀妻,有遗男,始龀,跳往助之。寒暑易节,始一反焉。河曲智叟笑而止之,曰:“甚 矣,汝之不惠。以残年馀力,曾不能毁山之一毛,其如土石何?”北山愚公长息曰:“汝心之固,固不可彻,曾不若孀妻弱子。虽我之死,有子存焉;子又生孙,孙 又生子;子又有子,子又有孙。子子孙孙,无穷匮也。而山不加增,何苦而不平?”河曲智叟亡以应。
操蛇之神闻之,惧其不已也,告之于帝。帝感其诚,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,一厝朔东,一厝朔南。自此,冀之南,汉之阴,无陇断焉。
五柳村据〈三思科学〉版本制作
来源:人民网(责任编辑:许秀华)